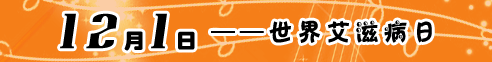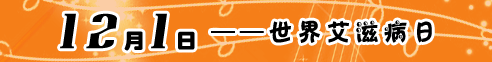神秘的“4号楼”
4号楼,没有想象的神秘。
4号楼很不起眼。跨进紧锁的铁门,穿越塑胶的羽毛球操场,右拐,再经过习艺培训间,一座5层的小楼就是了。
4号楼也有名字,叫“康复楼”。是全省唯一收治男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专管中队。
所有强制戒毒劳教学员都会在这里短期停留
李孟春所长说:“戒毒人员送到所里后,首先进行艾滋病初筛检测,对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戒毒人员,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本人告知。每年还邀请疾控中心专家给艾滋病戒毒人员举办艾滋病防治专题讲座,组织医务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发放一些慰问品。”
除指定的管教民警和戒毒人员之外的任何人,很难获准进入。
所有强制戒毒劳教学员,一般都要在这栋楼进行短期的停留。所有落所新来的,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后重新编队,进入常规中队。
而有一部分人不会这么幸运,他们是学员当中最不守纪律,常常不服管教的人,会从常规中队出来,投放到这里重新编入严管中队。
这两队人马,一是因为“新来的”,二是因为“老油条”,而被许多学员所注目,除了用作谈资之外,他们不愿接近。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接近的机会,这栋楼,单独管理,单独操练,单独劳动,单独作息。
严管队在三楼,手上有着刺青的学员刘东(化名)指指头顶,说,4楼的人才可怕。
4号楼4楼,颇为神秘。5楼是空着,为了腾出地方接待可能更多的艾滋病强戒劳教学员的到来。作为全省唯一接受男性艾滋病戒毒学员的地方,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上,之前,这里一度也收押了女性艾滋病学员,因为管理的尴尬而转移到另一监所。4楼65人,是历来人数最多的,而马上,又将有一批转运来的5名患者到所。
从2003年11月至今,4号楼已经收教艾滋病强制戒毒隔离人员200多人次。
他们集中于外省籍,浙江本省人仅仅两人。西南的贵州人占了半壁,其次是云南、四川还有新疆。
在毒品猖獗的西南,他们在当地就开始了吸毒史。
政委罗爱民描述,这里的戒毒者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外省籍在浙打工人员——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吸毒——感染了艾滋病”。
我省研究毒品犯罪的一位警界资深人士称,西南在浙的涉毒犯罪严重,而且云贵等省份的吸毒者在浙“潜伏者”众。
一套门禁系统隔开了两个世界
戒毒者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米,4楼宿舍和电视房,1楼的生产间和教室,再就是门口标准的篮球场。吃饭,有食堂师傅会专门一车车拉来。用餐后,所有饭菜容器将送到收容点,单独消毒保管,排泄物也都每日进行及时消毒处理,所有生活用品和理发工具专人专用。
结实的门禁系统将长排生活区与楼梯隔开,坐在门口的值班室,目光所及直到尽头。值班室里的监控操作台上,每一个探头都忠诚地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王警官,曾经艾滋病专管中队中队长,如今是分管艾滋病中队的副大队长。掏出磁芯门牌开门,带着记者走进去。右边是谈话室,一旦有心理问题,便可以在这里接受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劳教民警的谈话。
紧挨着的是电视室。每天晚上7点,雷打不动地集体按时收看“新闻联播”。
407室有几位值日学员在谈天,看到王警官,迅速起立报告。他们区别于常规中队,全部住下铺,因为怕上铺意外跌落受伤出血。被子整齐地叠成了方块豆腐。
一楼,工作间。
看到有陌生人突然进入教室,他们都把目光朝向记者,手头上的习艺培训活儿停下,记者有点不好意思了。
在此之前,这里禁止对媒体开放。他们互相嘀咕着,这是谁来了?
出乎记者的意料,他们大多并不虚弱,没有羸弱到气若游丝,也没有枯瘦如柴,相反,记者的身形在队伍里算是十分瘦弱的。
李孟春说,艾滋病的潜伏期长至12年以上,现在接收的戒毒人员一般都在感染5年之内。没有病发,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但免疫力相对弱一点。
但如果病发,他们就像点蜡烛一样,一烧完,生命终结。

电话是艾滋病戒毒人员与外界维系的纽带
混江湖的他,厌倦了江湖
东奇(化名)喜欢称自己是蜡烛,他每天睁开眼睛都会自嘲:哦,蜡烛还没有灭。
3日,是他农历生日,这位浙江南部某县的青年的而立之年。
一身江湖味,“玩过多少女人”、“偶尔打K粉”、“跟着老大看场子、抢地盘”,“开店生意不好就关了”,上述记忆碎片在他嘴里平淡无奇,犹如咀嚼过的青菜梗子,构成了他30年人生之前的主要回忆。
在这个盛产富翁的南部城市,东奇的家境也算殷实。读到初一,一次一如既往的考试过后,他撕毁了试卷,跑到父亲跟前,说“我不读书了,我想早点学做生意!”
排行老三的他最受父母疼爱,他的父亲可能至今为他做过的决定懊悔不已。
最害怕晚上熄灯那一刹:明天,我会醒来吗?
东奇开始混“江湖”。现在在戒毒所,他也最爱看一些武侠小说。
“我喜欢跟比自己成熟的人玩在一起。”他叫隔壁村一个朋友“大哥”,如同港片里的画面,在一个破烂而隐秘的房间里,他摊开锡箔,拿着“大哥”的ZIPPO打火机,幽幽地点燃了第一口海洛因。
和所有64名艾滋病感染吸毒者一样,他的解释是因为好奇。
经过初次“头重重的,想呕吐”的吸毒体验之后,他着上了海洛因的道。
跟大哥,当老大。抢地盘,看场子,收入不菲。但开销也大。“做老大的,总得给弟兄们分到好处,比如,做一单10万,得分个5、6万给弟兄们快活。”
所谓的快活,是开始在KTV、夜总会里喝酒、打K粉,寻找女人。
“我从来不找街头洗头房里的女人,一般跟一些酒吧里的女人一起玩,大家有感觉了就过夜了,从来不戴套。”在东奇的感觉中,这些女人都很“高档”,怎么可能会有艾滋病,连性病的顾虑都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玩过多少女人。”说这句话,东奇没有半点炫耀,双手握紧,眼睛望着窗外,因为从未针孔注射过毒品,东奇认定,自己是通过不洁的性交感染上的,究竟是谁?
“就等于在热锅里寻一只6条腿蚂蚁,不确定。因为每一只蚂蚁,都是6条腿。”东奇状态很好,具有江湖的“不怕死”气质,乐观,不忘记跟记者这样打趣。
他们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更是特殊的病人
这个“江湖”让他身陷艾滋病之扰,他开始厌倦了这个江湖。
如果前几次进强制戒毒隔离劳教所,还有出去复吸的可能。这次,他坚决地说了“不”字。他清楚自己的身体,虽然艾滋病毒在体内潜伏最多不超过3年,但他决意停止毒品,“吸下去,等于更快死。”
因为免疫能力较常人弱,东奇在戒毒隔离期间数次感冒,常人不吃药都能好,他吃了药也好得慢。他很感谢这里的劳教民警,在全部公费医疗的环境里,获得了较好的救治。
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罗爱民说:“现在的执法理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艾滋病戒毒人员不仅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同样是‘病人’,而且是特殊的病人。特殊病人的双重意义在于,他们吸毒,经常幻觉,脑损伤,有精神疾病,另外,他们是艾滋病感染者。”
想起小时候过生日妈妈做的红烧肉
这里作息时间与外面不同, 4号楼一天的生活——
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做一些轻微的习艺性劳动,午饭后安排午休,下午进行适度身体训练和体育运动,晚饭后自由活动,可以下下棋、看看书什么的, 7点收看新闻联播,9点熄灯。
中午10点半吃饭,这天,他特意打了份红烧肉,因为小时候过生日,妈妈会给他做红烧肉。
应该还有7个月,东奇将解除劳教,回家是他最想的事情。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他说要陪着一直爱自己的女友去做检查,如果有,就“拿起男人的气概”告诉女友,一起过下去,我负责到底。
如果没有感染上,东奇说,会跟她“拜拜”。
“我不会吸毒,但也许还会玩女人,风花雪月不可能避免,但至少,我会戴上套子。”东奇面对浙江在线记者抛出的“出去后,你会不会将艾滋病毒再传染给别人?”这个似乎敏感而直接的提问后,飞快回答。
“人心是肉长的,我即使在江湖里混,但不会主动去害人,再说,传染艾滋病毒也是犯法。”
东奇跟记者握了握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拜托记者隐去真实城市和姓名,起身离开,回到他那个40公分长的习艺培训操作台去。
东奇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伙食不错,有肉吃。一些简单的习艺培训打发了无聊的时间,阅览室的书籍发到每人的手上,轮流交换着看。
他最害怕每晚的熄灯那一刻,望着偶有光亮的窗外,他担心,明天还会醒来吗?
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