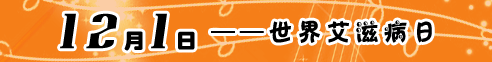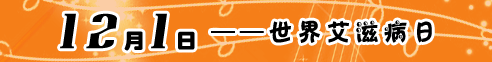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我现在已经想开了,其实艾滋病并不可怕,但我最怕病情被别人知道!”一位艾滋病患者日前与本报记者展开了一次面对面的坦诚交流,情到深处,她几度哽咽,泪流满面。
前天上午,郭红如约出现在瓯海区疾病控制中心,远远地站在走廊边上的角落里,见到记者时,她面带怯怯的笑容,从外表上看,都与一般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
这时,瓯海区卫生局局长郑国华一行特地前来慰问,当郭红接过生平第一笔慰问金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捧着慰问金不停地道谢。
今年40多岁的郭红家住瓯海区,十年前与丈夫离异。去年,在出国务工期间,她被查出患了艾滋病。回国后,她一直在家接受免费治疗,目前在市区一家鞋厂打工。
记者想跟她握手,那一刹那,郭红迟疑了一下,之后伸出三根指头轻轻地握了握,马上就缩了回去。“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一直不敢和别人握手。”她轻轻地说。
希望能活到60岁
几年前,郭红经人介绍,出国做起了“淘金”梦。在国外务工期间,为了替儿子和自己后半辈子着想,她拼命地工作,打算赚一笔钱后风风光光地回国。
然而,去年年初的一场持续20多天的咳嗽,彻底破灭了她的梦想。“有一天早晨起床后,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一直咳嗽个不停,老板知道后马上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医生认为我得了肺炎。”郭红只好停下手头的工作,安心接受治疗。
一晃20天过去了,郭红的咳嗽症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咳得越来越厉害。这时,她感到问题有点严重,于是就请老板带她去另外一家医院重新检查,结果,她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知道这个结果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记者问。“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郭红摇摇头,“医生跟我说我听不懂,老板又不敢告诉我,只是说我的血液查出来不大好,在国外治这种病的费用很高,要我马上回国接受治疗。”
就这样,郭红伤心地踏上了回国的征程。随后,在市有关部门对归国人员的例行体检中,她被告知患上了艾滋病。瓯海区疾病控制中心获悉后,马上对其进行了免费药物治疗。
“当时我就想到我完蛋了!”郭红泪涌了出来,“我听别人说起过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会死的。我死了,出国时向人家借的七八万块钱怎么还?儿子还没成家怎么办?”
记者劝她:“得了这个病,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心理负担。资料上说,如果坚持吃药控制病毒,可能一辈子都会没事的。”郭红掏出纸巾不停地擦着眼泪:“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最希望能够活到60岁。”
怨自己没有防范意识
“能说说你是怎么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吗?”记者小心翼翼地绕到这个话题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郭红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
“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的,对你来说不可能存在母婴传播,你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属于哪一种?”记者试着帮她分析。她想了想,终于开口了:“我在国外跟过一个男的,是中国人,我们在一起有一年多时间。”
“那个男人知道你得了这个病吗?”
“知道。他说他后来也去查过了,没有被感染,其实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我也搞不清楚。”
“除此之外,你还有跟别的男人交往过吗?”
“还有一个是介绍我出国的那个男人,后来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说着说着,郭红的眼泪又不听使唤地掉下来,她说自己从来不用避孕套,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男人把病魔传染给她。“说实话,一个女的长期在国外,没有男人在身边是很难生活的,”她哽咽道,“这没什么好恨的,大家都是自愿的,要说后悔,只能怨当初自己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郭红在国外期间,为了治“肺炎”几乎花光了积蓄,回国后,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她的前夫知道她患了艾滋病后,主动收留了她。“我担心把病传染给他,吃饭、睡觉全部分开,后来我病情稳定了,找到了一份工作,前夫也有了新的女人,我就搬出去了。”提起前夫,她的眼眶里又噙满了泪水。
药品藏在垃圾桶里
记者见到郭红这天,她恰好要到瓯海区疾控中心取药,“治疗这个病的药都是中心免费提供的,以前10天领一次,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我来去不方便,就叫我一个月来领一次。”在旁的工作人员告诉郭红,这一年下来,这些药总共要好几千元,她马上惊讶地叫出来:“这么贵啊?如果要自己买,我肯定没钱买的,如果这样那我干脆就不治了。”
“你到这里拿药,有人知道吗?”记者插了一句。“没有人知道,每次我都是一个人悄悄地来。”郭红无奈地笑笑,“拿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药盒烧了,然后把药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藏在屋子角落的垃圾桶里,就怕别人发现。”
“平时家里客人多吗?”记者问。“除了儿子偶尔来几趟看看我,从来没有人来过,”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就是怕万一有人知道我得了这个病,老板如果不让我上班,那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儿子知道你得了艾滋病吗?”提起儿子,郭红眼泪潸然而下:“我不敢告诉他,也不敢让他发现这些药,不过他好像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可能是我的前夫告诉他的。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想办法把他办出国,到我以前的那个老板那里打工,多赚一点钱。”
瓯海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郭红接受了一年多时间的免费药物治疗后,目前病情趋于稳定,现在,她体内的一种叫CD4的免疫细胞活力明显增强。
郭红告诉记者,现在,她除了吃饭胃口稍微差一点外,其他各方面都跟过去一样正常,“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疲劳,不过最担心的就是得感冒,稍微有点症状,我就得马上打针吃药。”
想买台电视机作伴
在持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郭红将手中的信封不停地揉捏着,信封里装着刚刚送来的1000元慰问金。终于,她等不及了,当着记者的面掏出钱一张一张地数着。“哇,好多啊!”话音未落,她忽然哭出声来,用来擦泪的一张纸巾被揉成碎末。
“我可以去买一台电视机了!”她止住泪,脸上又出现了一丝笑容。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她除了五度哽咽落泪外,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晚上一个人回到家,也没有人说说话,9点多就睡觉了。有时候一想起就整晚睡不着,买台电视机,也好有个伴。”聊着聊着,她无意中捋了捋前额稀疏的头发,“如果没有得这个病就好了,你看,就因为整夜睡不好,现在连头发都掉了很多。”
采访结束时,记者提出能否到她家里看看,郭红连忙摇摇手,眼神中带着些许企求的意思,“千万不要过来,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我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好吗?”
记者手记
第一次与艾滋病人面对面接触,我主动与她握手,双方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感觉这是一次很普通的采访。然而,看着郭女士几度哽咽泪如雨下,讲述自己的不幸、无奈与困惑,我却好几次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刹那间,我真切地感受到,艾滋病人实在是太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关注了,他们需要社会多一点关爱,少一点歧视。
提起艾滋病,许多人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恐惧、陌生和好奇的心理。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艾滋病人往往不敢公开病情,不敢面对公众,这是目前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记者在文中舍弃了很多诸如她与工友交往、走亲戚等细节,郭红也再三交代,千万不要让人从某些细节中猜测到她的身份,因为她怕失去本来就很狭小的生存空间。
郭红刻意隐瞒病情,从不敢主动与人握手,去饭摊吃饭时,从来都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角落边上。其实,只要没有血液的直接接触,握手、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根本就不会传染艾滋病,但在一般人的眼里,很可能就会如临大敌。她反复问记者:“难道这样也会传染吗?”
如今,郭红接受免费检查和免费吃药后,病情已趋于稳定,身体也不像过去那样感到累了。她开始为将来打算,为儿子筹划着未来。在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能多活一天算一天,但保证会像正常人一样地活下去。
相关链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定今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为“遏制艾滋,履行承诺”,目的就是为了督促世人开展以预防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遏制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
1981年,自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的感染者及艾滋病人逐年增加,目前艾滋病的感染正以1.6万人/天速度发展,全球已有1630万人被艾滋病夺去生命。
我市自1985年首次检出HIV感染者以来,截至今年10月底共有32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67例就发生在今年1至10月份。近两年来,我市的艾滋病病例报告数以平均每年30%至40%的速度在快速增长。同时,感染者有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
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透露,我市目前被感染者中青少年居多,性传播、吸毒传播仍然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
2005年4月,我市启动辖区内艾滋病人抗病毒治疗工作,开展艾滋病自愿免费咨询检测工作,24小时开设咨询电话。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医疗专家协助下,确定治疗对象,负责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建立个人档案,并按计划定期随访,保证抗病毒药品及时免费供应发放。
为进一步加强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力度,目前我市已建成艾滋病初筛实验室21个,确证实验室1个。该艾滋病实验室的投入使用,可使我市艾滋病确证时间缩短一半。
目前,艾滋病患者接受的免费治疗药物主要包括国际常用药物核苷类、非核苷类药物,像蛋白酶抑制剂、司他夫定、齐多夫定等等。这些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必须终生服用,还必须遵照医嘱服药,如果自己乱用药,就会产生耐药性,必须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