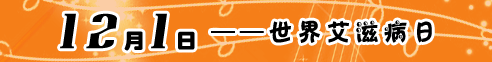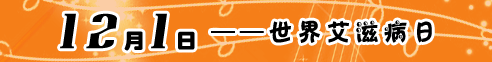2008年12月1日是第二十一个世界艾滋病日,新一轮以“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为主题的防艾全民战争打响。云南省各界以不同形式掀起防艾主题宣传活动,本月和下月已被定为云南省“新一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宣传月”,有关部门在昆明市各个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防艾知识宣传活动,图为昆明市民驻足于防艾知识宣传栏前,学习防艾知识。 中新社发 杨洋 摄
孟林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药盒。10点整,铃声响了,孟林站起身来,“对不起,我吃药的时间到了。”
孟林从药盒里拿出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一种是蓝色,就着开水服下。“一天两次,要准时。”他说。
十多年来,孟林就是用这种方式,顽强地抵抗着身体内病毒的袭击,也提醒着自己的特殊身份––艾滋病人。
除了药物副作用和工作压力导致略显黑瘦外,孟林外表看来与常人无异。然而,作为北京“爱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的负责人,孟林比许多普通人更为忙碌––每月出差到4至6个省市,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办网站,写博客,编杂志,接受采访或者约见病友……恰值不惑之年的他,对进出的每个人都报以谦和友好的微笑。
“我来讲讲我的故事吧。”孟林说,声音始终低沉而压抑。
中国活得最久的艾滋病人
除夕夜,他被赶出了家门,“自生自灭”。 他目睹了身边病友的离世:没有亲人,没有医护,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能有个氧气瓶就已经很好了”。
孟林是1995年底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的。早在那之前数年,他身边已有朋友因艾滋病离世。“我这一辈子,与艾滋病斗争了13年,却与艾滋病的恐惧斗争了20年。”
13年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艾滋病的治疗水平与知识普及都远不及今日。1996年初,当孟林拖着腹泻、皮疹和全身淋巴肿大的病体来到北京佑安医院就诊时,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无药可治。
其时,那个后来被誉为“鸡尾酒疗法之父”的美籍华人何大一,还在实验室里紧张地进行着研究。而在佑安医院,这家中国著名的传染病医院,尚未建立专门的艾滋病科室,更遑论病房。
幸而佑安医院决定开展一个由徐莲芝医生主持的中药抗病毒实验,将太平间旁边几间原本用于收治麻风病人的平房用作临时病房,于是,孟林与其他几名艾滋病人一起住了进来。那是一排阴暗低矮的房子,在当时却意味着希望和生机。
3个月的治疗成效不错。更为幸运的是,几个月之后,大洋彼岸传来喜讯,鸡尾酒疗法问世。在国内尚买不到药的情况下,1997年初,徐莲芝帮助孟林联系到了一名美国医生,并采购到一些药物,孟林幸运地成为国内最早一批用上鸡尾酒疗法的病人。“遇到徐阿姨,是我一生的幸运。”孟林说。
正是徐莲芝帮助孟林走过了那段最为灰暗的时光。孟林永远不会忘记,1996年除夕,当他鼓足勇气向家人坦白自己的病情后,便被赶出了家门“自生自灭”。那个万家团圆的深夜,他却独自泪洒街头。从那时起,孟林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那种颠覆的感觉刻骨铭心。”
那几年,就连许多医生也对艾滋病抱有不恰当的恐惧。住院期间,“血常规、胸片等很普通的检查项目医院都不肯做。多数情况下,医生只是拿着一个听诊器来看看。”每到晚上,为防止这些病人“跑出去危害社会”,医院会将他们反锁在屋内。
孟林目睹了身边一些病友的离世:没有亲人,没有医护,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能有个氧气瓶就已经很好了”。这样的情景一再重现,给孟林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对生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亲情的渴望,交织在这个当时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心头,令他几近崩溃。
是徐莲芝大夫将他拉了回来。无论是治疗还是生活,这位慈祥如母的传染病专家给了孟林最大的关怀。1996年5月12日是孟林的生日,徐莲芝在送给他的一张卡片上这样写道:
“为儿唤起心中的彩虹,送上慈母的深深祝福,祝儿生日快乐!健康愉快,岁岁平安!”落款为“母亲”。
这张卡片至今放在孟林的办公桌上,用相框精心封装。他在贝利马丁奖的获奖感言中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我出来为其他病友做了一点点事情,不为别的,只为妈妈想起有个叫孟林的儿子时,她感到自豪!”
“呼吸就有希望”,在与病魔斗争13年后,孟林将这句话作为自己博客的标题,他也已经成为国内发病后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
逼出来的志愿者
“颠覆”又一次降临。他长期苦心经营的“双面人”生活被击碎。电话几乎被打爆,朋友们的质问、责怪纷至沓来。如今,“北京孟哥”已经成为艾滋病人圈子中颇具名气的人物。
2003年,国家启动包括免费抗病毒药物的发放、免费病毒抗体初筛、提供救治关怀等在内的“四免一关怀”行动,让艾滋病感染者看到了生的希望。
“现在的情况比起那时不知好了多少倍。”孟林说。十几年来,他亲历了中国艾滋病防治体系从无到有艰难前行的几乎每一个步骤,也亲历了社会对于艾滋病的认识由歧视到相对宽容的点点滴滴。
2003年起,陆续有相关方面找到孟林,希望他作为一个“过来人”向刚刚开始接受免费治疗的病人们“现身说法”,起初都被他拒绝。那个时候,他运营着自己的一家公司,也以此支撑着自己高昂的医药费用。公司里和朋友圈中,没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人。“我只想清清静静地过日子。”
直到2004年10月,国家某专门从事艾滋病防治的机构找到孟林,想让他在“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中负责一个名为“爱之方舟”的论坛,与病人做在线交流,他答应了。
论坛的工作地点最初设在这家机构。孟林到那里去了几次,一开始感觉不错。然而不久,一天午饭时间,他向别人问询食堂的地点,得到的回答竟是“你不能在这里吃饭”。
一个专门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国家级机构竟然无法容忍与病人共餐,这让敏感的孟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气之下,他选择离开。
不过,“爱之方舟”论坛的工作,孟林一直坚持了下来。2005年起,在一些专家帮助下,孟林和他的小组在佑安医院感染科病房内找了新的工作地点,在这里,他编辑《我们的声音》杂志,并将“爱之方舟”逐步扩展为一个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获取信息、相互联系的自助组织。
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长久。“颠覆”,在2005年底又一次发生。
在一次感染者摄影展上,孟林一分多钟的发言镜头被一家电视台在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播出,他长期苦心经营的“双面人”生活被击碎。电话几乎被打爆,朋友们的质问、责怪纷至沓来,“你为什么欺骗我们?”
孟林无力回应。他关掉了原来的手机,也关掉了公司。这次事件成为孟林迈向一名专职艾滋病工作志愿者的转折点。
“聪明、有脑子,有水平。”1996年起便与孟林相识的隋雪英护士,这样评价孟林。
近4年来,孟林他们组织了多次主题研讨,帮助全国各地建立起近40个感染者互助小组,如今还承担着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北京孟哥”已经成为艾滋病人圈子中颇具名气的人物。
经常会有各地病人来找他,他都一如既往地给予帮助。“我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因为我经历过。”今年年初,病友紫阳患上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病情恶化且治疗费用高昂,孟林通过博客、邮件和各地组织发起呼救,前后筹款近十万元,帮助紫阳渡过了难关。
孟林给自己的“爱之方舟”提出的工作目标为:社区能力建设、政策倡导、促进中国感染者工作网络化建设。“实践证明,感染者组织在参与政府主导的艾滋病防治体系中,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目前,孟林正在为二线药物的引进和普及奔走呼号。国际上用于艾滋病治疗的抗病毒药物共有28种,根据效力和价格的不同,分为一线、二线、三线药物。2003年起,我国开始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药物,常见的6种都是一线药物,对于那些早期服药的人,耐药性已经开始显现,更换二线药物刻不容缓。但药物的升级,不仅意味着价格的大幅上升,还包括来自国外药企知识产权的阻力。
孟林呼吁,必要时及时启动强制仿制程序。“当前情形已经到了万分紧迫的时刻,许多病人再一次站在生死线上。”
当慕容枫碰上孟林
那些回忆如同刀子,一次次剖开他的伤口。“说实话,我不愿讲我自己的故事。但只要听众愿意听,我就会讲下去。我希望这可以让他们看到一名感染者的真实一面。”
与孟林不同,来自河北的慕容枫,从噩梦开始的那一刻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2005年初,一次单位组织的无偿献血中,他被查出HIV阳性。未等市疾控中心来作确认,血站就将他患病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慕容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懂得了什么叫人言可畏。他患病的消息在几个小时内传遍了单位和社区。同事相见,远远地躲着他走,社区的网站上,竟然有人将他的信息贴出来,警告大家“这个人有艾滋病,离他远一点。”
在这之前,他是当地机关的一名干部。市里的青年突击手,省里的优秀团务干部,挂满光环的他前程一片光明。艾滋病击碎了这一切。
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市疾控中心医生好心地对他说:“要不帮你出一个证明辟谣吧,就说你其实是乙肝大三阳,你还可以继续上班。”慕容枫拒绝了。
在那之后的一年中,他同每一个感染者的最初阶段一样,恐惧、抑郁和绝望。幸而家人没有拒绝他。开明的父母不仅接纳了儿子,也接纳了儿子的病友。由于被暴露,一些病人开始悄悄与他联系,他的家逐渐成为病友们的聚集点。在这样的交流中,他渐渐接受了现实,决定勇敢地站出来做点什么。
2007年3月,慕容枫通过一名病友认识了孟林,二人第一次打电话就聊了40多分钟。电话彼端孟林传递的信息让他兴奋不已,“忽然发现北京还有这么大的组织,这么好的资源”。在与身边感染者商量后,慕容枫决定成立“爱之光”感染者互助社区,寓意希望每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能生活在爱的阳光下。即刻,他动身去了北京。
他在北京郊区通州租了间房子,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北京所有他能得到消息的培训和活动。在一次次交流和听讲中,他开阔了眼界,也大大减少了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他决定用这些知识来帮助其他病友。2007年夏天起,慕容枫在孟林和北京佑安医院福燕护士长的帮助下,陆续为几十名病友建立了免费检测关系。11月,他又回到河北搞了一个治疗培训班,25个人参加,效果不错。
从2008年开始,除了做好感染者治疗关怀外,慕容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普通人群推行艾滋病知识普及和消除歧视宣传上。他开始频繁出入社区与学校,在全国做了几十场演讲和宣传。每到一处,他都先以志愿者身份向人们宣传,再以感染者身份与人们进行交流。即使在出租车上,慕容枫也从来不避讳与艾滋病相关的话题。
“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社会就不可能了解我们,真正理解和帮助我们。总要有人站出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每到一处,慕容枫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讲讲你患病的故事吧。”
面对提问者好奇的目光,慕容枫会耐心地、一点一点地从头讲起。他总是带着阳光般的笑容告诉观众,“艾滋病,只是意味着我们的血液和别人不同,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对社会有用的事,同样可以坚强、健康和快乐地生活!”
事实上每讲一次,他都会哭一次。那些回忆如同刀子,一次次剖开他的伤口。
“说实话,我不愿讲我自己的故事。但只要听众愿意听,我就会讲下去。我希望这可以让他们看到一名感染者的真实一面。”
说这话时,刚过30岁的慕容枫满脸灿烂,却灿烂得让人心痛。
歧视,不可承受之重
更多的歧视深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一名大学生感染者在北京打工,老家的县级疾控中心的人,开着消毒车全副武装冲到他家,进行全面消毒
孟林与慕容枫,两个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草根”,因为同一种病毒,面临着相似的境遇。“反歧视”是两个人共同提及最多的字眼。
切身经历让他们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反歧视远远不及一个握手,一个拥抱那么简单。”
孟林的父亲迁坟,他不能与家人一起走,他租了一辆车远远跟在后面,直到所有人都走了,才敢上前。作为儿子,他连触摸一下骨灰盒的权利都没有。
慕容枫的妹妹结婚,作为哥哥的他却不敢出现在婚礼现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向外人提起有这个儿子。
“与世界上很多传染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相比,艾滋病的治疗情况甚至还要优越许多。艾滋病作为绝症之‘绝’,往往不是绝了‘命’,而是绝了‘情’。”一名志愿者在“爱之方舟”的内部通讯上这样写道。
更多的歧视深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手术难,就是艾滋病感染者面临的诸多困境之一。
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传染病医院是收治艾滋病人的专门性医院,但传染病医院毕竟不是综合性医院,一些特殊的治疗手段和手术条件并不具备,而普通医院则往往将HIV阳性者的手术拒之门外。
2008年春节,孟林的一名病友在放鞭炮时不慎伤到眼睛,急需手术治疗却四处碰壁。几经波折,一家以收治艾滋病人为特色的著名医院终于同意为其手术,但前提是病人必须配合电视台做直播宣传。
病人犹豫了,“我暴露了倒没什么,但我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啊……”手术前的一天下午,病人接到通知,手术取消。
无奈之下,病人只得通过私人关系,由一家传染病医院出病床,外请眼科医生进行手术。但手术器械却要病人自己四处去买。由于耽搁过久,这名病人的眼睛出现感染,眼球最终被摘除。
一些基层卫生部门对待艾滋病的态度还远远谈不上开明。
孟林亲历过这样的饭局:一名负责卫生工作的基层官员并不知道孟林就是感染者,在饭桌上称“感染艾滋病的没一个好东西”。
一名大学生感染者毕业后在北京打工,今年夏天查出HIV阳性,老家的县级疾控中心从联网信息中得知这一消息,开着消毒车全副武装冲到他家,进行全面消毒,并对好奇的村民说,“其实是不应该告诉你们的,但是出于保护你们的目的……”
慕容枫说,这名感染者目前已经勇敢地走出阴影。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也没有再回家。
“一个病人就会影响一批病人对于社会的态度”,孟林忧心忡忡地说。艾滋病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非常弱。反歧视,最重要的是让这批人获得平等就医、就业和就学权利,“不能把他们推向社会的边缘”。
成长中的“草根”
面对民政注册高不可攀的门槛,一些互助社团试图走工商注册的路子。“事实上,我们非常愿意在政府的监管下工作,希望让政府看到我们的努力。”
11月26日,孟林与慕容枫一同走上了贝利马丁奖的领奖台。
2000年,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创办的贝利马丁基金会设立了这个奖项,用以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8年之后,该奖项首次颁给艾滋病患者。
这也是孟林今年以来获得的第二个奖项。今年9月,他与姚明、李希光等人,共同获得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
“感恩不是简单的报恩,它更是一种责任,自立、自尊和追求一种阳光人生的精神境界。”孟林在获奖感言中这样说道。慕容枫则称,这个奖给了他鼓舞,也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约而同的,孟林与慕容枫都将所得奖金捐献了出来。前者以个人名义设立了“徐莲芝奖”,后者则设立了一个“爱之光”基金,用以奖励那些为艾滋病奔走呼号的人。
事实上,他们自己更需要支持。作为完全自发成立的民间互助组织,无论是“爱之方舟”还是“爱之光”,实际运行中都面临重重困难。
首要的问题是资金。目前,国内大多数抗艾民间组织都依靠向政府、国际基金会申请项目维持生存,国内企业和个人捐助极少。这其中,来自国际基金会的资金又占了相当比重,他们自嘲为“喝洋奶”。
但现实中,“洋奶”并不好喝。“我们是在协助政府做事情,协助政府做宣传,逐步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接纳。”慕容枫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反复强调这一点。
但对于大多数草根组织而言,目前甚至无法实现身份的社会认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民间社团要在民政局完成注册,就必须找到局级以上主管单位,拥有固定办公地点,但鲜有单位愿意为一群艾滋病人的自发群体承担责任。
面对高不可攀的门槛,一些互助社团试图走工商注册的路子。上个月,“爱之方舟”刚刚完成工商注册。“但这意味着我们每收到一笔捐助或拉来一笔资金,就要交纳相应税款。”孟林说道,“事实上,我们非常愿意在政府的监管下工作,希望政府能看到我们的努力。”
孟林说,未来几年里,他计划写三本书。一本是“百名艾滋病感染者访谈录”,计划通过对一批感染者的访谈,真实反映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现状和困境。第二本是“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组织发展简史”,通过对草根组织的深度访谈,反映出这些群体的现状,为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第三本则是“感染者权益维护手册”,要从政策法规、伦理等各方面为HIV阳性人群提供系统帮助。
“无论如何,我希望为社会留下一些资料,相信多年后,这些资料不仅仅记录下中国抗击艾滋病的历史,也将成为研究中国公民社会早期发展的有益参考。”
孟林说出这句话时,神情像极了一名社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