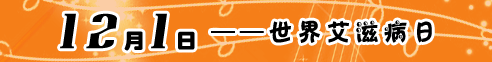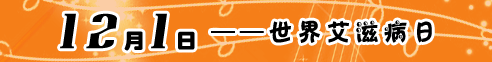徐莲芝已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却不像大多数老人一样颐养天年。因为她是中国治疗艾滋病的顶尖权威,人称中国艾滋病首席医生。病人们爱戴她,亲切地叫她徐妈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称她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徐莲芝说:我们虽然为病人解除了一点痛苦,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看着“艾滋狼”在疯狂地吃人,作为医生却无可奈何,没有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了。
由于妈妈的病痛和弟弟的夭折,徐莲芝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医生。她说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既是自己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幸福和快乐。正是这种信念,使得她对如狼似虎的艾滋病无所畏惧。
在我小的时候,妈妈的身体不好,饱受病痛的折磨,以致若干年后我回忆起妈妈时,总是看见她在大把地吃药,听见她那痛苦的呻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四岁的弟弟又因病夭折了。现在回想起来弟弟的病就是消化不良症,根本不至于死人的,就因为庸医误命啊。困顿时,人就会产生幻想,当时我就想,假如我们家有个医生,假如我就是医生,能治疗各种疑难病症该有多好啊!那样,妈妈就能摆脱病魔的纠缠,弟弟也就不会被误治而死了。
所以在后来报考大学时,我第一志愿是学医,第二志愿是学医,第三志愿还是学医。从拿起听诊器的第一天开始,我便在心中立下一个承诺: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既是我的工作和责任,也是我的幸福和快乐。
自从1990年接治国内第一例HIV感染的出国劳务人员以来,我已亲手治疗了几百例艾滋病患者。当时有关艾滋病的知识还不够普及,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接触这个病。看见我无所畏惧地向前冲,一些人不解地问我,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我确实一点也不害怕,这倒不是因为我胆量有多大,更说不上觉悟有多高,而是我的专业和性格让我不怕。我是搞传染病的,与各种传染病人打了四十多年交道。艾滋病算得了什么,它不过属于乙类传染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流行性脑炎的高发期,它是经呼吸道传染的疾病,传染性更强,送到医院的病人都是昏迷状态。每遇生命垂危的病人我们都会本能地拽下口罩实施人工呼吸。过后最多只是漱漱口,吃一点磺胺类药物以防万一。虽说这样做太危险,不宜提倡,但作为医生必须具备这种精神,和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危急时刻要敢于冲上去,随时作好献身的准备,这是天职啊。
当然,我还是关注自己健康的,每年坚持体检。就是工作起来顾不上许多。前不久,我手指不慎弄破了,贴上了一块药布我就去查房,倒是我的病人大惊失色地喊住我,让我马上离开这儿。
我的患者中有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就因为在当地拔牙而感染艾滋病。在非洲工作时,他接受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上街须三个人同行才能获准,他根本没有机会行为不轨。但没有人听信他的解释。他丢了工作,失去朋友,连亲属都不愿和他来往。他饱尝精神和肉体折磨,最后想报复一些人就自杀。后来他在咨询中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尽最大可能关心他帮助他,使他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一份报告中所说:“我们必须继续与视艾滋病为耻辱的观念进行斗争。把艾滋病藏在耻辱的幕后反而会帮助它的蔓延。勇敢地说出有关艾滋病的问题才能减慢它的传播速度。”
我总共接诊五百多次,HIV呈阳性的只是一百多例,很多人都是自我恐惧,自我怀疑。因此排除说服非患者,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一次一位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如约前来,说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央求我给他确诊治疗。他言辞恳切,声泪俱下,说自己在某个场合与一个女子有了性接触,不久后便发烧,消瘦,食欲性欲减退。他认定是得了艾滋病,又不敢去医院求治,已经强忍了八个月。我说你亲近的人中谁最了解你?他说是妻子,我说明天你和妻子一起来,我给你做全面检查。在体检中我发现他的肺部有问题,准确地说有一侧的呼吸已经听不到了。转院后不久,他妻子告诉我他已被确诊为肺癌。可他在手术后仍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坚称自己是艾滋病,希望转回我这里治疗。
1996年春节前,在单位的新年聚餐会就要开始时,有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助,同事们都希望我能参加聚会,说春节后再约吧。我婉拒了大家的好意。每位艾滋病患者都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敢来就诊的,必须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因为他目前仍在接受治疗,不宜暴露真实姓名,就叫他H吧。
他非常焦虑地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年仅二十八岁,是同性恋者,近来经常发烧,全身乏力,淋巴节肿大,他的性伴中已经有人患艾滋病。
经过抗体试验,为阳性。他确是一名艾滋病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对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医患之间的第一次交谈非常关键。要多用关切启发式语言,要给他们指出希望的所在,要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我们是可以信赖并能给他以帮助的人。
看着我手里的检测报告,H一脸恐怖,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停地向我追问结果。为了尽量淡化他的阳性反应,我平静地说:“因为你早有思想准备,不错,正像你想象的那样。”不等我往下讲,他哭了,低着头抽泣不止:“徐阿姨,我可怎么办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H的电话。他声音模糊,像是喝醉了酒,说是要和我作最后的告别:“让我最后叫您一声‘妈妈’吧,希望您能大声地答应我,我现在特别想妈妈。这世界上已没有几个人挽留我,我知道这样做很对不起您,但我还是要走了……”我急了,问谁在他身边,他说小万在身边,我说快让小万接电话。我严肃地警告小万,H的安危由他负全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叫一辆车把H送到我这里来。小万还算听话,他采纳了我的意见。
我立即穿好衣服,出门去迎他们。
当时已是11月份,站在瑟瑟的寒风中,我有一点发抖。很多人说我从事着一项艰难的工作,与医生的概念相去甚远。我却不以为然,只要是工作就总得有人去做。在深夜的寒风中焦急地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我才体会到了一点所谓“艰难”的滋味。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成了我的住院病人。在他生日的那天,我亲手做了一张贺卡,上面画了两颗心,为写那一句话,我想了许久:“心灵的力量是永恒而不可战胜的。”
一晃三年过去了,一直坚持治疗,病情也比较稳定,为筹措治疗经费,他开了一家专卖装饰画的商店,生意还不错。他家里人也早已和我取得联系,在确定帮助他的办法时就和我一起商量。现在H每周打来一次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每次我都叮嘱他少喝酒,不要吃冷食物。
为了让艾滋病患者有一个沟通畅叙的地方,我们特意腾出一间病房作为“常回家看看”的活动园地。艾滋病感染者或他们的家属,包括已经接受治疗和尚未接受治疗的,都可以参加活动。活动的宗旨就是沟通信息和思想,互相倾诉,彼此鼓励。后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心家园”。H每个月都到爱心家园来,帮助我做新病友的思想工作。有的人或碍于情面或性格孤僻,不愿意来,不愿意交流,我们也不勉强。与癌症患者一样,心胸开朗,积极配合治疗,与性格封闭不能配合治疗的,存活时间和治疗效果都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曾接诊过一对艾滋病患者夫妻,男的急性发作,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就死了。我帮助他的妻子小冯料理完丧事,建议她也去医院查一查,不料,她却跟我吼起来:“我们的灾难已经够多了,我还有十岁的孩子啊。”
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外资企业的中方代理,我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以后,她和我说了真心话。我很高兴,因为让艾滋病人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她谈到自己天真烂漫的童年和青春岁月,谈到她曾经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还谈到她奋斗的坎坷与艰辛,最后她谈到死亡谈到孩子,她说:“真没想到您会对我这么好,使我再想到自杀就觉得惭愧,觉得对不起您。我虽然给孩子留下了房子和部分财产,但我不知我委托的人日后能否尽心地照顾好我的孩子,如果您能替我……”
我不想让她再说下去,赶快岔开她的话题。不是我自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是很好,实在不敢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不能兑现的承诺,对双方都是难以解脱的折磨呀。
后来小冯去世了,在帮助她料理丧事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不幸而又可爱的孩子——婷婷。两年前我送走了她的父亲,现在又送走了她的母亲。看见孩子,让我既心痛又内疚。
孩子很懂事地走过来给我鞠躬,说徐奶奶我早就听说您了。我握着孩子的双手说:“好孩子,今后要保重自己,要好好地生活,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来找我。”
以前每送走一位艾滋病人,我就与他们的亲属断绝往来,但这次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冷血,而是我得替人家着想。每个艾滋病患者,都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烦恼。病人一旦去世了,他们的生活才能逐渐恢复平静。我又何必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呢?
在小冯夫妻俩相继去世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提着一盒月饼去看婷婷,还让她作了体检。所幸的是,她最终的血检结果呈阴性,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做医生几十年,徐莲芝就忙了几十年,从未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所以有人说她是没有自己时间的医生。假如真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会做什么呢?
我们全家都是搞医的,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日常生活十分简单,家里的陈设大多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古董,一张几十块钱的旧饭桌,用了近三十年也舍不得扔。我肯定不是出色的家庭主妇,好多事我都做不来,就拿做饭为例,我常做的就是煮面条。只有孩子们回来或有亲戚朋友来,才郑重地做几样饭菜。
好在我和爱人在大学时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做了四十多年的医生,我突出的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知识不够用,病人的痛苦总是让我心绪不宁,牵肠挂肚,惟有不停地工作才能慰藉我无能为力的歉疚。
目前有一点时间都用在写书上了,已先后出版了《艾滋病临床病例图谱》、《实用艾滋病治疗指南》等书,现在正在整理典型病例。好在除工作之外,没有其他嗜好。文艺、体育都不行,只有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喜欢而已,一直没有机会受专门训练。但这毕竟是我有待实现的心愿,有画展什么的我总想去看一看。
除医生之外,只有绘画最适合我。我早就想好了,等我真的不做事了,就一定去学绘画,我相信是能画出一点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