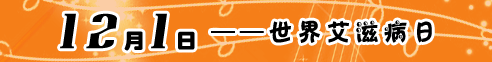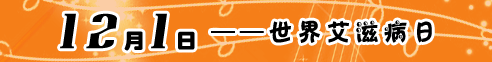一旦被诊断出艾滋病,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健康、生命,甚至还有尊严和人格。目前,柳州已经发现多例艾滋病患者,他们的境遇如何?今报记者走近了他们。
我要回家
关门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他的一声尖叫:“我要回家!”主任说,他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柳州,星期天早晨,北风潇瑟,寒雨浸骨。
一家医院的朋友小吴,把我带到传染病房。主任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刚刚查完病房,右手戴着一只手套,说是天冷,手开裂了,戴上手套以防意外。
主任和小吴把我带到艾滋病人的病房。尽管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也早就知道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空气和一般生活接触传播,但是,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艾滋病患者,恐惧依然无法避免,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在微微颤抖。小吴问我是不是有点害怕,我没有作声。
9号床的艾滋病人独自住在一间病房,一根铁线把门锁缠死了。主任一边解着铁线,一边对我说:“这个病人原来是吸毒的,毒瘾经常发作。发作的时候,到处乱跑,现在走不动了,就爬着出来,所以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推开门,只见病床上那个人面色黑黄,颧骨高耸,嘴角糜烂,目光散淡,神情恍惚。
“我们来看你了。”主任和小吴靠近他,我跟在他们身后。
“哦,好啊!”他眼睛亮了一下,声音飘飘的。 “你感觉怎么样?”
“痛,全身都痛,动都不能动。”
主任说,这个病人已经出现并发症,全身免疫系统不行了,五脏六腑被病毒严重侵蚀,前段时间发烧呕吐很厉害,这两天用了一些药,稍稍缓解。不过,只是暂时的。
他今年34岁,住在柳州市荣军路,家里只有两个亲人:母亲和姐姐。他静脉注射吸毒多年,家当早就被他吸空了。母亲气出一身病,3年前就已瘫痪在床,年近40岁的姐姐操心不已,至今仍孤身一人。没钱买毒品后,他就去抢劫,后来被捕入狱了。
11月10日,他被狱警送进了传染科。一查,发现是患了艾滋病,而且出现了并发症。主任说,他的病是静脉注射吸毒感染上的,估计生存时日不多了。
姐姐来医院看过他,得知是这个病,很绝望。她是普通工人,辛辛苦苦挣到的钱还不够家里的基本开支。要给他治病,一天至少得花上六七十块钱,要命的是,这个病根本无法治愈。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留在医院。
“想家吗?”
他沉默不语,眼睛空空洞洞地望着我们。我们默默地离开了他的病房。关门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他的一声尖叫:“我要回家!”主任说,他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怀念从前
“我不怕死,但是我害怕别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你千万不要写我的名字,好吗?”
9床的隔壁病房还躺着两个男性艾滋病患者。
4床是来自柳江县里雍镇的病人,正打着吊针输着氧气,看上去情形和9床相差无几,不同的是他的身边有几个亲人陪着,一个是姐,一个是哥,还有一个老人是他的姨娘。主任说,像这样有亲人陪在身边的实在稀少。
“知道你弟得了什么病吗?”
“肝硬化,肺气肿,好像还有别的病吧?”四床的姐姐说。
“如果他得了艾滋病,你们还会来陪他吗?” “不可能是那种病!我们都住在农村,农村不可能有那种病!”
这位姐姐一脸的惊恐和疑惑,她认为艾滋病只有那些作风不正派的人才会惹上,但医生明确告诉她,他弟弟是因为静脉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的,现在已经到了晚期。
病人的姐姐和哥哥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一直以为弟弟内脏有病,没想到会病得那么恐怖。不过,他们表示,不管弟弟怎样,他们都会陪在他身边。“我们是他的亲人,要是我们丢下他不管,就不会再有人理他了。”姐姐的眼睛红了。
浓眉大眼的6床是鹿寨人,看起来显得比较年轻健康。见我们走进来,他冲我们笑了笑。不过,笑容有点勉强和无奈。
他说自己今年30岁了,两个月前,感觉全身无力,呕吐不止,一直发低烧,在鹿寨县医院作了检查,发现得了甲肝和丙肝。
“这种病特别麻烦,医生说很难治,要我来柳州看一下。我到这家医院门诊抽血作了检查,第二天就转到传染病房来了。”停了停,他突然问我们:“不会是艾滋病吧?” 主任说:“还没有最后确诊,你别多想。”
“那今天有个医生说,我可能得了艾滋病。我问他是不是有了结果,他支支吾吾的。我急了,就对他说:‘你说话要负责任,如果我不是艾滋病,那你可不能乱说,这样对病人会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你们说是吗?”
“假如是呢?”
“是就没办法了,唉。”他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艾滋病有初筛期、窗口期、潜伏期、发作期,我到了哪个期呀?是不是窗口期?”看来他对艾滋病了如指掌,对自己的病情似乎也心里有底了。
其实他早就被确诊了,现在已经到了发作期。 “你怕吗?”我轻轻地问他。
“怕也没有用,这条路是自己走的。”
他是1998年上“路”的。那时他26岁,自己搞运输,钱来得很快,有时一个月可赚上万元,至少也有好几千块。一个夏日的晚上,他跑车回来,感觉有点疲惫,想睡觉,来了个朋友,还带了白粉。那个人叫他尝尝,他没有拒绝,吸了一口,“感觉灵魂一下子飘上了天堂”。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由鼻吸改为静脉注射,身上的血管都扎遍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瘾君子”。几年赚来的钱转眼灰飞烟灭,最终成了穷光蛋,未婚妻也离他而去了。
“白粉真的是魔鬼,被它缠上了就脱不了身,只有死路一条。” 他说,要是让人知道他得了这种病,病毒还没来得及将他消灭,旁人的唾沫可能就先把他淹死了。 “要是能重新来过就好了。”他自言自语。他说非常怀念吸毒以前的日子,怀念那曾经拥有过的甜蜜爱情,温暖的家,健壮的身体。而这一切,正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
“唉!”与我们告别的时候,他重重地长叹了一口气。
爱莫能助
什么时候艾滋病人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呢?那一天,或许很远,或许很近。
“这些病人的结局都是惨不忍睹的。”走出病房,主任告诉我。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他们传染科就收治了二十来个艾滋病患者,有些病人送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到了发作期,不到两个月,就去了。
这些病人大多数是男性,只有3个女子,90%以上是因为静脉吸毒而感染上的。因家产被他们耗空,亲人大都对他们绝望了。况且得了这种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一家人根本就没法活下去。所以有的把病人送到这里后,丢下一句“随便你们怎么处理”就再也没了踪影。于是,吃饭、用药都是医院负担了。
“我们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主任告诉记者,以他们目前的医疗水准,根本无法对抗艾滋病毒,他们只能对病毒引起的局部感染作些处理。 “有些病人被社会和亲人遗弃了,我们这里就成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驿站,所以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单是资金方面就已不堪重负。”主任告诉记者,每收治一个艾滋病人,他们要倒贴四五千块钱。
“你同情他们吗?”
“怎么说呢?想起他们是因为吸毒才感染上这种病,觉得有些可恨。但作为一个生命,应该同情,何况我是一个医生,更应该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多一点人道主义关怀。” 主任说,他们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患者,给他们以常人的同情和关怀,但是,目前难度很大。 “别说是艾滋病人,就是跟别人说我们在传染科工作,人家都会远远地避开。要是知道这里收治了艾滋病人,其他病人不吓跑才怪。”
在传染科做了二十多年护理工作的护士长说,她已经习惯了。1996年,柳州市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就是她护理的,那时还不知道那人得了艾滋病,等到确诊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
“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好在没事。”
护理艾滋病人,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特别是冬天,给他们打针,那可真要小心翼翼,因为冬天护士们的手很容易开裂受伤。
我看见一个护士给4号床打针。病人因长期静脉注射吸毒,身上的血管全被糟蹋了,变得跟铁丝一样坚硬。要找一个能扎针的地方,实在不容易。打针的护士只好脱下手套,轻轻地触摸血管,找准了,再把针慢慢地推进去。
“为什么脱下手套?”事后,我问护士。
“戴着手套不方便,针扎不准,增加病人的痛苦。” 其实正常护理护士们都不怕,怕的是那些脾气暴躁、不讲道理的病人,特别是那些抱着“我是艾滋病我怕谁”态度的患者。
“今天7月的一天晚上,大概有十点多了,有个病人说要吃白切鸡。值班护士说这么晚了,哪里还有白切鸡呀。那人不管,一定要吃,护士没办法。他就拿起一把水果刀,唰唰地朝板凳上砍去,把我们的护士吓得脚都软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做心理护理,和他好好讲道理,他听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护士长说,毕竟是一条生命,走到今天,他们已经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何况,到了这个份上,他们的生命去日无多,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待他们好一些。
从医院出来,小吴给我讲起另外一个艾滋病人的遭遇。那个男子被确诊患艾滋病后,家人把他送到偏远的山村,租了一间破旧的泥房,让他一个人住了进去。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药物,没有亲人。他就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人生:孤独,恐惧,绝望,痛苦……
什么时候艾滋病人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呢?那一天,或许很远,或许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