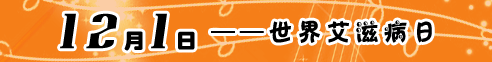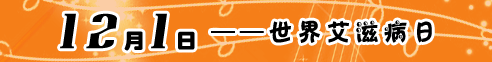“冰冷,特别的冷。当我第一天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后,我感觉异常的冷,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濒死的体验,反正当时我就是那样的感觉。在我30多年的人生里,我遇到过挫折、困苦、失败,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绝望。”
“我当时以为在我面前再也无路可走,死亡似乎是唯一的结局。但佑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用实际行动让我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只要听从医生的科学指导,服用抗病毒药物,我们一样可以健康地生活。如今,我像平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只是每天多了一项按时服药,和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患者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一刻对我来说,既是死亡,也是重生。如果没有这件事,我想我还无法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的定义。不管遭遇什么,都应该好好地活下去。”
在北京,有很多为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工作的公益小组,大志和他负责的“绿色”工作组算得上是其中比较知名的。虽然大志在公益领域颇有名气,可是他的为人却非常低调。
初中毕业他就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标准的工人阶级。那时的他也交往过几个女朋友,有的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大志总感觉什么地方不那么对劲。
29岁,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同志,才知道世界上“这样的人”原来很多很多,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再和同志朋友的交往中他感受到了真诚、关爱和幸福。
2004年,他不幸被确诊为艾滋病“阳性”患者,躺在佑安医院的病床上,突然之间就直面“生死”,心有凄惶,几经绝望。
2006年,他积极筹建了现在的“绿色”工作组,在社群中为广大病友一点一滴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宣传国家的政策,介绍新的药物,进行心理支持和关怀,组织社群活动。他的工作组先后参与了全球基金第6轮项目和中盖项目,现在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也快批下来了。
正值不惑的他,经历了几番人生的折腾:工作、入圈、同居、分家、确诊、病退、到最后成立工作组,这些在一般人眼里“离奇”的经历,他都一一扛过来了。现在虽然每年还要住上一段时间的医院,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情,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乐此不疲。
而当我面对眼前这个40岁的男人,看着他那没有一丝掩饰和虚伪的笑容,听着他再次揭开自己的伤口侃侃而谈时,我看到了一个生命的善良、热情、真诚和宽容。
LH:你从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同志的?
大志:1996年,我29岁,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分水领。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还有这圈子,只是和同事有过这样的接触,心里有种隐约的渴望。
96年12月底,在陶然亭(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点”)那,遇到一个27\8岁的小伙子,他是我第一个接触的“陌生人”。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我们这样的人。以前只以为自己是,觉得不正常,现在才知道是自己见识少。
LH:你后来交过几个朋友呢?
大志:有过2、3个吧。 97年底,我在玉蜓桥下认识了小衡,一周后我们的感情加深了,就去分种寺那租房,住在了一起。他的家人也都支持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过了2年多,和普通的夫妻一样,没有任何不同。
2000年底,我在樱花东街遇到了小陈,26岁,重庆人,来北京找工作。觉着彼此很合适,我们就去南苑租的房。虽然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他对我的情感经历很有意义,他特别照顾我,走道都让我在里面走,怕我被车碰了。我们彼此付出很大,真的完全象一家人一样。
LH:在你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后,还交过男朋友吗?
大志:说来也奇怪,在我确诊之后交往的朋友无论是外在条件还是性格,都非常的优秀。我从来不隐瞒,但他们还真的不在意,只是我们会特别注意性行为时的安全。我想两个人在一起,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感情,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LH:那你是什么时候出柜的?
大志:1998年。当时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我嫂子早就说过我是“同志”了,所以当时他们也没怎么大惊小怪的,家里人也知道我肯定是不会结婚的。但我妈向我提了个要求:要找个子高点的、长的不错的、有工作的;最好还是北京的,这样如果你们闹别扭,我们还可以去调解一下。呵呵。这条件有意思吧。
出柜后,我心理上轻松了不少,也再也没有结婚的压力了。虽然家人也担心我老了没人照顾,但这才是我需要的生活和情感,我很坦然也没有顾虑。
LH:在你确诊艾滋病后,和家人关系怎么样呢?
大志:和原来一样啊,没有任何变化。血缘这东西就是那样的根深蒂固,我妈很多时候反而劝我,说现在医疗水平那么发达,以前认为是绝症的都可以治疗了,让我要有信心。我想她也是想让我开心吧。
我和朋友都见过对方家长,虽然他们开始有点想不通,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渐认可了,是真的在心理上接受了我们。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血浓于水吧。
现在我主要是和男朋友一起住,和家人一起住不方便,这和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一样吧。但我们住的离父母很近,还经常去他们那里“蹭饭”呢。
LH: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呢?
大志:2004年底,我去拔牙,拔牙之后出了很多脓血,医生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只是吃了点消炎药,可第2天就虚脱,老摔跟头。再去医院检查发现淋巴有结节,做手术前验血发现了这病,后来就转到了佑安医院,住了大半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恰好赶上了国家颁布“四免一关怀”的政策,要不然可能早走了。以前和我一起住院的早期的病友,没赶上这样的政策,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走了。
LH:那你现在用药的情况如何呢?
大志: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只要平时坚持按时服药,对日常生活基本不会有影响,和普通人生活是一样的。现在国内的药品品质和效果都在提高,我见过一个用药快20年的,活的好好的。
LH:刚发现时,心情起伏很大吧?
大志:是啊,最开始就是恐惧,死亡突然之间就摆在眼前,整个人都懵了,没着没落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但有时又胡思乱想,没有头绪。想想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人生才刚刚开始啊。再看看周围的人,很多人都很年轻,正值青年,生命之花却面临凋落,心里特别难受和绝望。
在这我要特别感谢佑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正是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这些在“鬼门关”徘徊的人感受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而国家颁布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和社会大众对我们这个群体的逐渐理解和接受,也在最大程度上对我们产生了最为积极的影响。
LH:在生命遭遇劫难、思想极度绝望的时刻,是什么让你能重拾生活的勇气呢?
大志:尊严。人活着必须有尊严,即使我们在死亡面前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尊严。
人要活的有尊严,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才能有希望,才会去为实现这尊严和希望继续走下去。当然,这肯定离不开关爱,国家的、大众的、医护人员的、所有人的关爱,这也是我最终决定成立工作组的原因之一。生命对生命的彼此关爱,才能让世界更加和谐;彼此温暖、不离不弃,信念不倒、尊严永存,这就是逆境和绝望中勇于面对、继续走下去的的原动力。
LH:你是如何产生了成立工作组的想法并付诸实施的呢?
大志:有这病的人都想着保命,哪还顾得了其他的事,过一天算一天。但后来我想,既然活着还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不能每天没着没落的,总要做些事,来证实自己存在吧。
再后来,我看到佑安医院下属的很多志愿者小组的人非常积极热情地参与到关心、帮助“阳性”人群的工作中来,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些和这病完全无关的志愿者都能为此努力,我为什么不能为病友做些事呢?经过反复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鼓起勇气从灰暗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开始为广大病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006年我成立了“绿色”小组,之前因为我在佑安医院的小组里工作过,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所以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顺利,我很愿意把这些经验和别人分享。
LH:工作组应该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大志:小组开始没有几个人,就我和在医院认识的病友忙活。后来不断有新人加入,工作组发展壮大了,又办了一个“平安”小组。我们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在丰台、大兴和宣武,很多志愿者也积极参与这份工作,不畏辛劳、真情互助。
因为我文化低,很多具体的事,比如写个项目书什么的,都不入门,多亏我们周围有很多公益组织(NGO),他们给了我们小组很多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协助我们完全了很多项目。
LH:现在还能感受到压力吗?
大志:我觉得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的一种“看法”——你在意它,就大;淡化它,就小。以前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周围人的反应,现在没那么敏感了,能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每个人活的都不容易,可生活一样还要继续。它是实实在在的,开心不开心,都是每一天。
工作组现在开展的很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对我们这一群体正面、健康、有效地宣传,普通大众才能逐渐减低对这病的恐惧心理,不再歧视,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有可能谈到别的问题——比如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
现在社会能提供给我们这一群体的资源越来越多,可以选择的领域不断拓展。看到很多病友能得到帮助,心理非常欣慰。这也算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吧。
我有信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政策的支持,社会的关心,越来越多的病友能健康、自信、快乐地生活,每个人的明天都将更美好。(文/LH)